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49)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陕工网(029-87344649)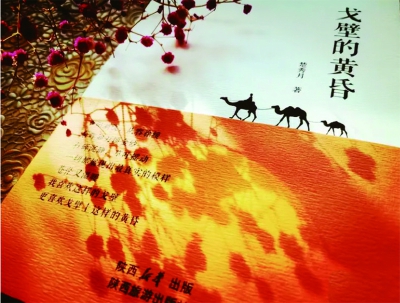
懵懂的少年,从原生家庭出离,变成天涯追梦的游子。又恰与家族迁徙史巧合,那生命的滋味该是多么波折。楚秀月就是那个漂泊者与追梦人。
因此,《戈壁的黄昏》绝不只是楚秀月的一篇代表性散文,也不只是以此篇名为书名的最后敲定,在更为深广的背景意义上,“戈壁的黄昏”注定成为楚秀月生命的隐喻和象征,它关乎着亲情、故乡、生命、生长、青春、思念与觉醒。与原生家庭割离太久,以文字退回回忆反复咀嚼,是她抚摸寂寞与暗伤的自带膏药。一篇篇散发漠北边地气息、追寻“生命原乡”的文字,无不饱含丝丝缕缕的深情与痛感。
戈壁的黄昏、冬雪的苍茫、故乡的往事其实就是作者的“生命自传”,是怀念袭来时无数次的“灵魂返乡”与“心电轰鸣”。
这样的散文是细腻而有张力的,具有明显的在场感与代入感。这“细腻”不是把话说尽的具象细化,而是善于捕捉记忆深处的幽微感觉,植入意识的飞动,使行文意脉自然游走在“虚”与“实”、“象”与“意”之间,瞬间情感返乡,激荡不已。
而楚秀月散文集已呈现出“大散文”气质,开头几篇堪称典型。这种“大”,首先是指篇幅的宏大、叙事的宏大、体量的宏大。当文字大幕徐徐拉开,在追溯延展中渐次跃出人、事、物、景,闪现情、思、理、悟,又有若隐若现的意识流动,于是“象”“意”“境”的浮沉变幻意蕴无限。
这种鸿篇叙事式的书写与意识流动式的内化使其文笔从一开端就跳出了同类题材同质化怪圈。她笔下的这些“恒常”叙事常常落入知觉与意识的萌动,生命成长隐秘的苏醒、觉察与幽微感知,字里行间氤氲着云雾般的现代意识。
宏大的叙述视野、舒缓的叙述节奏、妥帖的叙述声气、热切的叙述言辞,轻松抵达更久远更宏阔的叙事背景。过程以“忆”编织,以“象”铺排,以“情”统摄,以“思”收结,完成灵魂返乡。那广远深邃的天际,古老神秘的戈壁,苍茫无际的雪野,早已渗入作者的血液与骨髓,成为她生命最初的原始地。所以,在城市文明背景下的“精神返乡”就格外热切、鲜活、珍贵、疼痛,无不打着戈壁“黄昏”的时空印记,无不是对时光深处漠北人生的激情大写意。这些宏大叙事往往起于情绪,指向影像,全血复活后又落在意识深层,成为“意”中之叙,“念”中之事。作者往往沿着某种情绪郁积或物象触动,意念被打开,影像被唤醒、复活、演绎、重现,心绪在一幕幕一段段“往事”里纾放、平息、治愈。这样的文字治愈,在拥挤物化的现代文明背景比衬下,常常超越个体经验,上升到群体意识的普遍审视,一步步向“大散文”逼近。
但楚秀月散文的“小”亦不可忽视,这种“小”可以看作她语言艺术的一个切口:即她的散文,有一种小树发芽、伸枝展叶的气息。常常在文字行进中信手延宕,或一语双关,生出意味几重;或联想比拟,惹出留白几许;或顺手一击,引发人性审视;或突发奇想,逗出别样意趣。如:
“他们是冬季结的婚,过了蜜月,春天就来了。”
“不见祖母答应。风似乎把我的喊声刮走了。”
“用一张柳条编织的篱笆,把红薯窖盖得严严实实,像捂住大地的一只眼睛。”
……
这些刹那闪出的“小”,就像一朵朵晶莹透亮的浪花,划破鸿篇叙事的苍茫水面,在微波中闪动哲思诗意,改变阅读节奏,唤醒阅读沉闷。
而整本散文集随处散逸的现代意识尤其不可忽视。作者敏锐捕捉表现人的自我意识,从幼儿初始觉知到少年生长自觉,到青春意识苏醒,再到爱的朦胧觉知,试图剥开生命与成长的隐秘,所以从一开始就向深层写作挺进。文中的“我”作为客观生命存在,对美味的本能敏感,对最早走进生命的血缘亲近与依恋,交融着“我”的意识生长和家族命运变迁,使文本散发浓郁的“自传体”小说意味和现代意识。这应该根植于那辽阔、旷远、纯粹、单一而独具异质的兵团生态。
“我”总是在夕阳落幕的黄昏时间,一个人悄悄走出家门,走向辽阔无垠的戈壁,望向不知究竟有多远的远方。
这个反复出现的细节应该成为楚秀月散文的代表性意向,象征内在意识的朦胧觉醒与探索外部世界的隐隐渴望。它贯穿了作者整个青少年时代的成长记忆,既是久居异乡游子呈给“故乡”的深情诉说,更是拨开时间迷雾、探索生命奥秘、追溯生命印迹、触摸灵魂胎动的精神回归。
当她在故乡往事中不觉落入意识活动,便把通常情态的乡音、乡情的讲述者和记录者,变成感知者、参与者、反观者和思想者,因而字里行间渗透着她的意识流和生命感。这种现代意识写作,体现在她的散文叙事中总是向内寻求的,敢于大胆裸露隐秘的内心“真实”和生命“真相”,自觉抖落“载道”“教化”等附加值,更加贴近“人”学本身,成为生命苏醒与成长自觉的深层体认和自我肯定。
当然,这本集子后半部分篇章与前半部分似有较为明显的写作时序差异,尚需再度嵌入,深入把握,使之生出更深的滋味来。(张忑侠)
责任编辑:白子璐

关注公众号,随时阅读陕西工人报